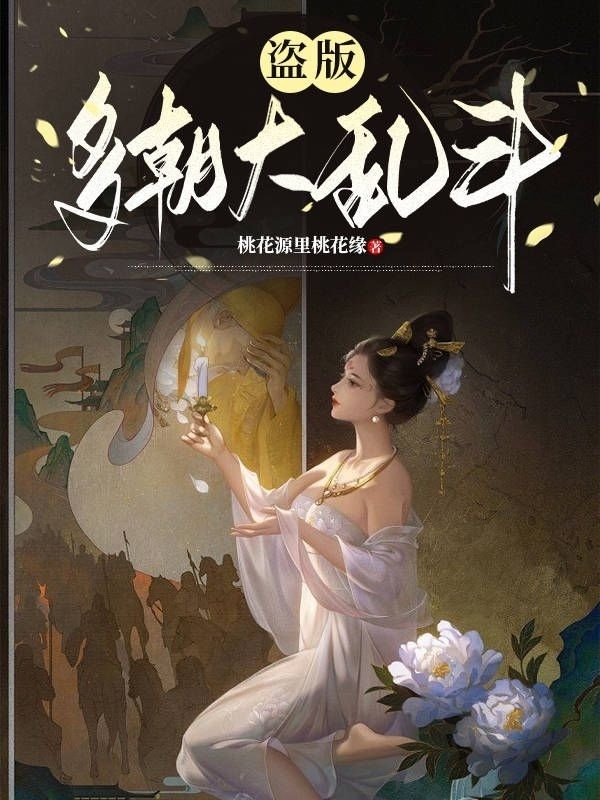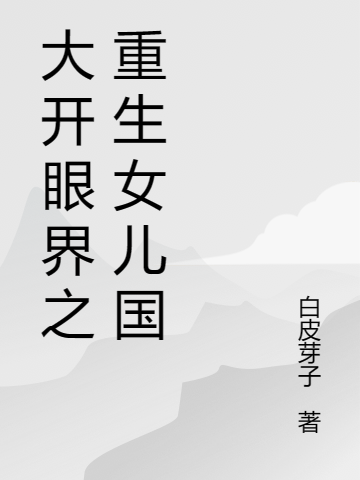太傅咳嗽一声,打断礼元千转百回的思绪。
老太傅捋着花白长须,严肃地道:“若是陛下再不上朝,恐怕老夫方才那番话已成事实!”
奶娘很适时的为太傅奉茶,太傅看在奶娘面上,态度有所缓和,很习惯地接茶落座。
礼元瞥了眼奶娘,故作惶恐地说道:“那可如何是好?”
太傅对礼元的反应很满意,欣慰道:“只要陛下明日上朝,散朝后请求太后宽恕,太后会给陛下一个改过机会的。”
礼元嘴角笑意稍纵即逝,长叹一声道:“果如太傅所说,太后真的能饶了我吗?”
太傅当即拍着胸脯道:“老臣担保!”
礼元重重拍了下桌子,大喊了一声“好”。
不待太傅凯旋而归的背影消失于眼前,礼元已经迫不及待的把披在身上的大氅拽了下来,奶娘心疼地说道:“天凉了,别冻着了。”
没办法,这不只是礼元的癖好,实际也是无奈之举。
“奶娘,都怪那个五石散,我热啊!”
此言非虚,常年服用五石散的人,隆冬数九也浑身燥热。
谈起来,这事儿得有六七年了。
跟礼元臭味相投的几个伙伴中,有一个在礼元心中的地位仅次于安蒙心。
方时,正儿八经的宦官子弟。
没错儿,宦官子弟。御马监掌印方立振,从族中过继来的这么个便宜儿子。
这俩算是和礼元玩的最好的了。
犹记得方时领着礼元和安蒙心第一次去青楼找乐子,方时神神秘秘地把这俩拉到一旁,拿出了那玩意儿。
从此,礼元便走上了这条不归路。
辽东方家,因为这位执掌兵符、统领禁军的方立振,从微末寒门一跃成为高门大户。
方立振虽是个阉人,却孔武有力。军中诸将对这位能为先帝当先锋的太监很是敬佩。
按理说,御马监循前朝之制,养马为其正职。先帝念方掌印鞍前马后,功劳殊高,令其执掌兵符,更是选拔辽东猛士入东园八营,供御马监统领。
这支真正上过战场,每个人身上至少背着十条人命的宫中宿卫,就连兵部也调动不了。
只听先帝的。
而把礼元引进不归路的方时,本是方立振的族中子弟。
作为一个宦官,方立振这辈子该赚到的都赚到了;但作为一个人,闲暇时,方立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
当然不是身上少了的那点儿。当了那么多年太监,身体上的缺陷,该放下的早放下了。
后来,方立振回乡省亲,看着兄长家满地跑的儿女,这才一拍脑袋,醒悟了过来。
于是,那次衣锦还乡,方立振办得最隆重的一件事儿,便是把族中子弟全都集合起来,跟那些个青楼女子一般,让子弟们排成一排,任他挑选。
方立振不看脸,踱着步子挨个上手试,可惜在方立振的天生神力下,没一个能经地住方立振随手一推。
方立振走到方时面前时,看着那豆芽一般的身材,摇了摇头。
也是方时合该在以后的日子里碰上礼元。在族中从来默默无闻的方时突然抬手拉住方立振。这位步战立斩二十三人的猛太监硬是被拉偏了身子。
从那天起,方时便成了方立振的合法儿子。
只是双手徒有四象不过之力的方时,在以后的日子里并没有满足方立振的期望。
那些个没当上方立振儿子,却愿意上进的家族子侄们,早已经在京营各部当上了武官。
但这个便宜儿子倒好,不愿习武,不识战阵,总之是不喜军中那一套,倒是愿意把一把子力气用在女人身上。
就因为这个喜好,方时不惜花大价钱,费大周折,才从士子圈儿里淘来五石散。
礼元后来才知道,前朝亡便亡在了这五石散身上。
礼元也是后来才了解到,先帝时常痛恨前朝宗室凋零,主少国疑,这才酿成忠臣惨死之惨案,终致亡国。他才勉为其难地当上了皇帝。
礼元隐约明白,先帝为何会努力耕耘,生了那么多儿子。
那些个饮酒赋诗,花前月下的士子,先帝管不了,也懒得管;但在军中和宗室内,五石散就是禁品。
一旦发现,笞杀。
也就是说,在知情人的眼里,礼元和方时早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。
倒是安蒙心,好歹出身将门,安敬思什么事儿都容着他,但就这事儿早有预防,安夫人这事儿倒是做到了夫唱妇随。
至今还记得安蒙心看到五石散时候的表情。
畏之如虎啊。
看着突然出现的安蒙心,礼元就气不打一处来,冷声道:“你小子,当时你既然懂这玩意是啥,怎么不拦着我!”
安蒙心也是早就习惯了礼元这赤条条的状态,正色道:“我来得及嘛我,我拦的时候你听吗?”
“罢罢罢!明儿以后就没闲功夫了,今日天儿还早,出去耍去!”礼元不耐烦地站起身来,奶娘已经把礼元出行的衣物准备好了。
马车直奔方掌印在宫外的别院,接上方时,然后一行继续往京城外而去。
方时刚上马车就从袖中掏出五石散,礼元也不避讳,抓起就嗑。坐在一旁的安蒙心不住地叹气,只得命两个小仆给礼元备好热酒。
“京城内外,该玩的都玩过了,今儿去哪?”礼元饮着热酒,随口道。
方时咧嘴笑道:“秋高气爽,咱哥儿几个好久没游东湖了!”
安蒙心点了点头,然后看向礼元。
礼元兴致正高,掀开马车帘子,高叫道:“好,那就游东湖去!”
王府内,奶娘盯着府门,面无表情。
今时不同以往。
往日游湖,那必然是排场宏大。
只要是能跟礼元玩得来的京城公子哥儿,有一个算一个,都叫上。
虽然,能叫上的,两只手数的过来。
除了他们,那是必有美妾作伴,乐师相随,再雇上京城外最豪华的游船。船入湖心,船内载歌载舞,船外鸥鹭齐飞,一众公子哥喝高兴了,倾美酒于湖中,在夕阳照映下,湖心泛七彩之色,真个诗意美景。
今日却只是雇了一艘小船。
倒也别有意境。
船上只有这三人,连船夫都让安蒙心撵了下去,方时自告奋勇做起了船夫。
终于到了湖心,方时一屁股坐下,喘着粗气道:“这么些年,真是把身子荒废了。”
安蒙心撇撇嘴道:“少用点五石散,比什么都好。”
礼元和方时俱大笑。
安蒙心满脸不解。
礼元极力远眺,看向湖边。
岸边,一众小仆已经小成了一个个黑点。
礼元这才放心说道:“这么多年,我俩能把你这个情报头子给骗了,那想必也能把那些个眼线给骗了。”
安蒙心恍然大悟。
方时敛容说道:“这么多年,礼元很辛苦。”
礼元摆摆手,面带愠怒地质问道:“安蒙心,太后可有立四哥的消息?若有,为何不报?”
安蒙心亦换了表情,很确定地说道:“这消息,子虚乌有,但另一个消息,现在想来,是我疏忽了。”
“讲!”我说道。
安蒙心习惯性地凑上前来说道:“你第一次上朝那天,退朝后,老太傅是和丞相并肩走出的宫门,二人有过只言片语。”
“为何不早报?”礼元冷声道。
安蒙心面带愧疚,喃喃道:“并不能知道太傅和丞相到底有何交谈;而且……”
礼元松了口气,缓和了语气说道:“这不怪你,朝臣之间有所交谈本是常事。何况,没有切实证据,这两件事并不能直接联系在一起。”
方时动了动嘴唇,但终究没有发话。
谈到正事的时候,这个宦官子弟总是很有分寸。
礼元看着方时,大方说道:“说,别憋着。”
方时看了眼安蒙心,欲言又止。
安蒙心眯起双眼,轻声道:“你是想说我爹的事儿吧,这个节骨眼,我们得开诚布公。”
只见方时灌了一口美酒,平静地说道:“前日大将军手段了得,事儿是平了,但不按规矩办事,安大将军要如何自处?”
安蒙心面色难看,但礼元这个没有任何实权的皇帝实在是有心无力。
礼元轻叹一声,拍了拍安蒙心,宽慰道:“朝中谏官,有多少人是郭相的门生,想必你比我清楚。我把你爹拔上来,本身是借了势,利用了朝中的现状,何况,也是我欠你们安家的。我为皇帝,你爹有资格做得了这个大将军!但若是事态失控,我还要委屈你们安家。”
安、方二人没想到礼元不仅没有责怪安敬思,话语之中还透着为大将军考虑的意思,先是一愣,接着又释然。
藏了这么多年,就连他俩都快忘了礼元原本的样子。
安蒙心不好表态,方时问道:“若朝中舆论对大将军不利,皇上准备如何安置安大将军?”
礼元当即表态道:“最坏的打算就是,把大将军外放。”
安蒙心面色凝重,刚要开口便被礼元打断。礼元微笑道:“无妨,我既然是皇帝,总不能让你们冲锋陷阵,我也该担一些了。”
安蒙心依旧没有就此事表态,礼元也不好再说什么,三人很默契地品起了美酒。
沉默了片刻,最终还是安蒙心打破了僵局,开口道:“家父能顺利接管京城各营,还是得了一个人点头。”
“王杰吗?”方时说道。
礼元吧砸着嘴巴,喃喃道:“酒,还是越老的越香啊。”
方时把头埋了下去,用近乎最低的声音说道:“老酒越喝越少,还是藏起来的好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