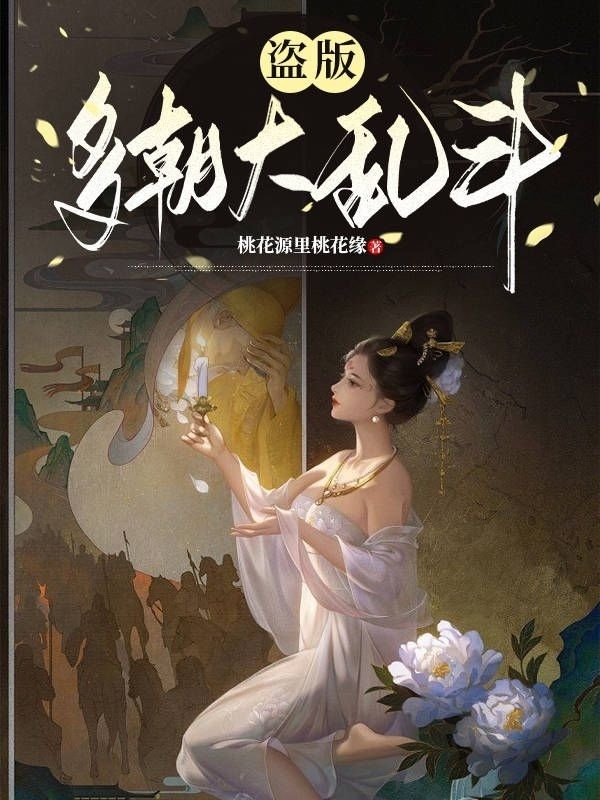“向营长,佐成!佐成!”
朦胧中听见有人在叫他,这是在梦里?还是已经到了阴间?
向佐成努力睁开眼睛,看见邱团长那张憔悴的脸。
“醒了,醒了!你娃命大!”
邱团长见他醒了,停止了来回走动,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。
原来向佐成被弹片击穿了脸颊,从左脸进,右脸出,在脸上留下两个血淋淋的洞口。手上和腿上也各中一块弹片,还好都是贯通伤,没伤到要害,炮弹爆炸的气浪把他震晕了。
“是他冒死把背你回来的!”
邱团长指着躺在另一张行军床上的李宏辉,他的军服被鲜血染透,人也早已气息全无。
“真是好弟兄啊,自己肚子中弹,硬是拼着最后一口气把你背回来,你娃儿永远不能忘了人家的救命之恩呐!”
邱团长感慨道,眼角溢出了泪花。
两行热泪从向佐成眼窝里涌出,脸颊的伤口使他嘴不能言。
他既哀伤又愧疚,一个营三百号人,最后只有他活下来。
向佐成一动不动地在团指挥所的行军床上躺了两天,眼前那些鲜活的脸孔不断在他眼前掠过。
外面炮弹爆炸声,子弹呼啸声越来越激烈,他知道鬼子的部队离指挥所越来越近了。
邱团长两天没有进指挥所,他一直待在战斗最前沿。
向佐成数次挣扎着想起身,但强烈的眩晕感让他最后只好放弃了。
第三天拂晓,向佐成听到指挥所外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,随后枪声乒乒乓乓响作一团。
少顷,邱团长带着一身硝烟味闯进来,他快步走近向佐成的病床,身边跟着两个卫兵。
邱团长不由分说,吩咐卫兵扶起向佐成,背着他向外奔去。
向佐成趴在卫兵背上,被颠得浑身疼痛,他忍不住叫了出来,想让卫兵把他放下。
跟在一旁的邱团长赶忙制止他,让他再忍耐一下。
终于,一行人在军马棚停下来,邱团长亲自牵出一匹白马,那是他的坐骑,安上马鞍,让卫兵把向佐成掫上马。
做完这一切后,邱团长似乎松了一口气,他调侃地说:“佐成,你娃儿命里遇贵人,前两天手下拼命把你背下尸山血海,今天长官我又要助你突出包围圈!”
他掏了掏口袋,摸出几块银圆,塞进向佐成口袋。
叹了口气,他声音忽然变得低沉下来:“此地一别,但愿你我有重逢之日。如我不幸战死,过年过节别忘了给我斟一杯酒,如果你也没跑出去,那咱们弟兄黄泉路上再见!”
说罢,他拉过一个卫兵,交代他道:“交给你个任务。你牵马往南走,一直走到有铁路线的地方,那是我军的防区,注意尽量绕开大道走,送向营长去安全的地方,听明白了吗?”
“听明白了!”
卫兵立正答道。
“好,我们走!”
邱团长带着另一个卫兵向着枪声依然激烈的地方大踏步奔去。
看着他们渐渐消失的背影,卫兵默默拉转马头,向反方向走去。
向佐成趴在白马背上,一路颠簸令他的伤口疼痛难忍,又不好意思告诉卫兵,只能咬牙硬挺。
天色大亮后,他们马不停蹄地来到了一片树林前。
前面突然传来马达轰鸣声,卫兵赶紧把白马牵进路旁的树林里。他怕马儿受惊暴露,用手轻轻抚摸马的脖颈。
白马似通人性般一声不吭,直到夹杂着摩托突突声的队伍从树林边一路绝尘而去。
“这是鬼子的摩托化步兵联队,我军没有,还好你没暴露目标。”
卫兵对着白马说道,一边爱抚着它脖颈的皮毛。
再次上路,卫兵变得更加小心翼翼,越靠近我军防区鬼子防守越是严密,随时都可能碰到鬼子的巡逻队。
他们一路走走停停,躲过鬼子的明岗暗哨,从拂晓走到黄昏,眼看就要到国军的防区了。
铁路线横亘在不远的地方,只要到那个地方就圆满完成长官交代的任务。
卫兵兴奋起来,拉着缰绳往前赶,眼看安全到达,他放松了警惕。
这时候,两个躲在树林里方便的鬼子哨兵从树林里有说有笑地走出来,和正经过树林的二人一骑打了个对眼,被他们吓了一跳,发现不是日军便怪叫着向他们追来。
卫兵一看避无可避了,他用力拍打着白马屁股,想让马先跑,谁知白马没有跑。
卫兵一下急了,对着向佐成喊道:“长官,抱紧马脖子,坐稳了!”
随后用上了刺刀的枪照马屁股刺了一下。
白马一声惊叫,撒开四蹄猛跑起来,向佐成拼命伏着身子,没受伤的手攥紧了缰绳。
他想转回头看一眼卫兵,但狂奔的马颠得他无法回头。
身后传来手榴弹的爆炸声,他什么都明白了,忍不住失声痛哭。
白马跑过铁路线,它没有停下,而是沿着铁路线一路往南跑下去。
炎热的天气加上一整天的疲于奔命,使向佐成的伤口火烧火燎般疼痛,他知道伤口发炎了,发炎引发的高烧让他时而清醒,时而迷糊。
终于,向佐成在马背上失去了知觉。
向佐成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,梦里和死去的弟兄唱着歌,一起坐着火车回四川去。
转眼到了家门口,父母亲还是老样子,家里多了个女人,他见过,是和他定娃娃亲的姑娘,她为什么会在家里?
向佐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,叫着父亲、母亲,可是他们看不见他似的,对他视而不见。
向佐成急了,去拉母亲的袖子,可母亲忽而一转头,露出青灰色的一张死人脸。
向佐成吓得大叫一声,从梦里惊醒了,他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。